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8-15 20: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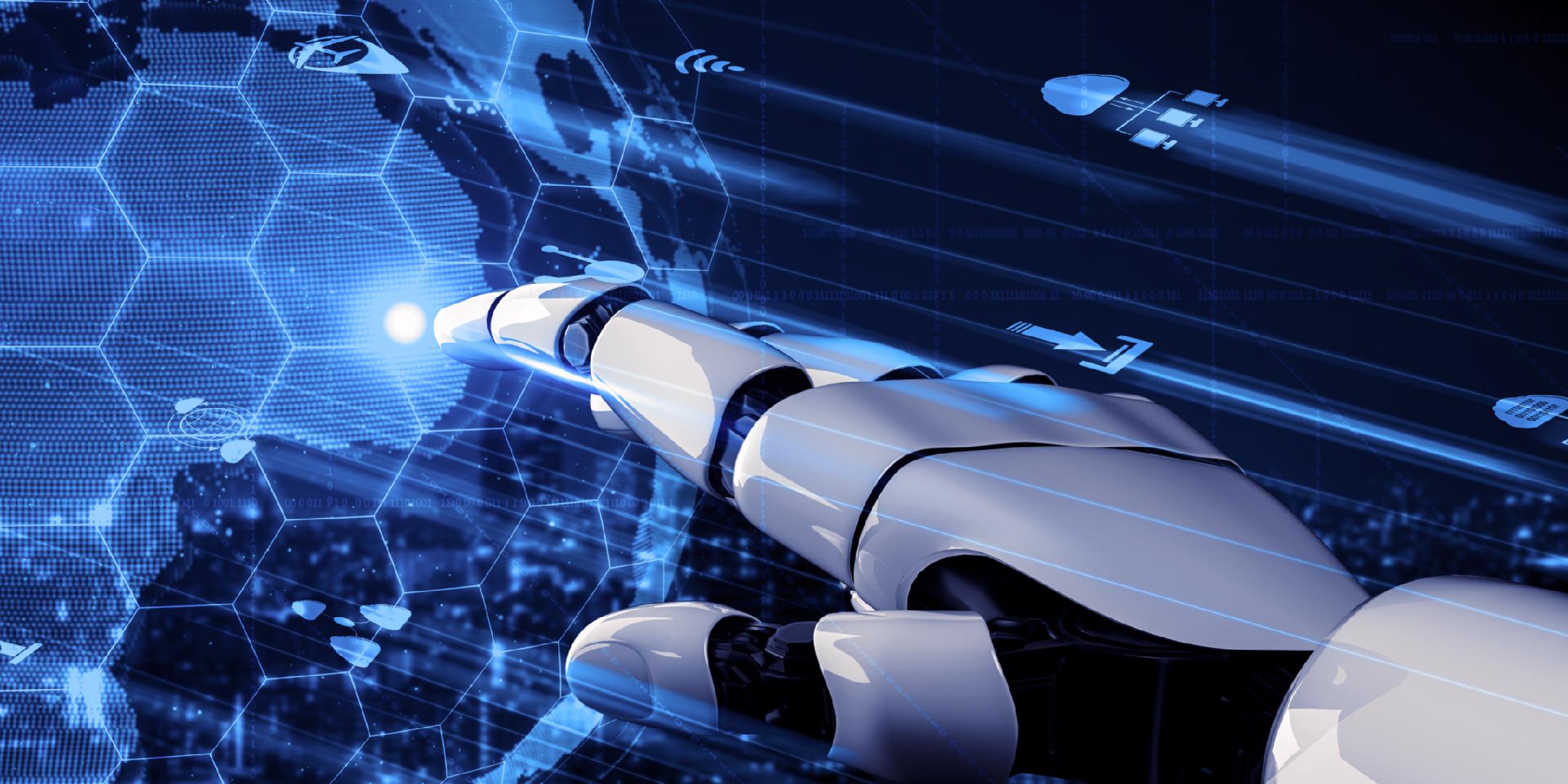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雅潔
一筆8.6億元的工程款,在一家基建央企的合并報表中“蒸發”了三個月——直到它最終流向一家失信供應商的賬戶,觸發了穿透式監管系統的紅色警報。
這是2025年國務院國資委推進“全級次、全鏈條、全過程、全要素”穿透式監管以來,捕捉到的數起風險案例之一。
這起案例,刺破了國企監管的薄弱環節之一:當資產規模持續攀升時,有時候,國資系統仍看不清錢去了哪里。
2025年6月,在株洲地區的國資委智能大屏上,31萬條資金流在實時跳動。
實時更新的光軌背后,是多次通過穿透式監管檢測出的數據“黑洞”。例如,2023年,一家市屬三級公司通過獨立ER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掩蓋5000萬元預付款逾期,導致全年1.2億元資產損失。
這不是個例。2024年審計署對國有資產管理審計情況顯示,在審計過程中,審計署發現了資產資金管理薄弱,使用績效不佳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產閑置浪費,二是違規轉讓出借,三是資金管理不嚴,涉及金額較大。
下沉基層,一家能源企業的倉庫里,同一批煤炭在7套系統中被稱作3種不同資產。
周姓物流負責人表示,財務系統記為“存貨”,物流系統標注“在途物資”,供應鏈平臺卻顯示“待驗收”。
5月15日,國務院國資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25年第一次全體會議首次明確提出要有序建立智能化穿透式監管系統,切實提升監管效能。
穿透式監管的概念較早出現在金融領域,2016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提出采取“穿透式”監管方法,整治互聯網金融行業各類違法違規活動。
2025年,國資監管系統打算構建的智能化穿透式監管系統,直指央企和國企全級次子企業的穿透式監管。
在重慶,“國資智管”系統將1901戶企業核心業務數字化率一度提升至98%;在航天科技集團,科研數據被劃入“監管黑箱”(科研數據使用過程不透明,難以被外部監管機構直接觀察),但資金流必須全域透明。
國務院國資委一名官員向經濟觀察報表示:“穿透不是要勒住企業的脖子,而是握住那根看不見的風箏線。”
經濟觀察報獲悉,目前,國務院國資委正在全面推進“全級次、全鏈條、全過程、全要素”穿透式監管體系,一場前所未有的數據革命正在國資系統內部展開。
另一名國務院國資委人士認為,穿透式監管的核心是“看得清、控得住”,而非“一管到底”。
以株洲為例,當地正嘗試劃定“監管負面清單”,市場競爭行為不予干預,但資金安全紅線必須全域穿透。
這場靜默的數據革命,正在重新定義“放得開”與“管得住”的邊界。
“跳動”的資金流
在株洲市國資委智能監管指揮中心,一塊巨型屏幕上跳動著密集的資金流圖譜——31萬筆支付記錄如血管般延伸至當地國資系統內的相關末梢子公司。
2025年6月上線的株洲國資國企資金監管系統,首次讓株洲市國資委副主任肖冬亮看清了“資金到底去了哪里”。
他說:“過去連二級公司的錢都盯不全,現在連三級子公司一筆超合同額的工程款都能實時預警。”
2023年的一次審計檢查,至今讓肖冬亮心有余悸。
株洲市屬某集團下屬三級公司一筆5000萬元的貿易預付款逾期未回款,而集團上報的月度資金報表卻顯示“一切正常”。直到對方企業進入破產清算,風險才暴露。
一名當地市屬國企副總經理說:“三級公司用獨立ERP系統做賬,數據從不向上同步。等層層報表匯總到集團,已是兩個月后的事。”
當年的審計記錄顯示,僅2023年,類似因數據滯后導致的當地資產損失已達數億元。
更大的痛點在于“監管失效”。
2024年,株洲市城發集團財務部長易谷秀發現,一家合作多年的建材供應商突然被列入失信名單,而子公司仍在向其支付貨款。
易谷秀表示,自己所在的企業,連對方企業信用變化都不知道,更別說穿透三級公司去攔截付款。
彼時,株洲市5家國企累計有1475家合作企業存在風險,但當地國資委既無實時數據接口,也無智能篩查工具。
轉機來自2025年3月的一場改革。
湖南省將“大數據防治隱性腐敗”列入省委首批重點改革任務后,株洲市紀委與市國資委成立聯合專班,目標直指“全級次穿透”。
第一步是“拆墻”。
技術團隊在調研時發現,在一家企業內,就能存在數套異構系統:用友NC、SAP、金蝶并行,子公司甚至用Excel臺賬應付檢查。每個系統數據口徑不同,連“應收賬款”的定義都有三個版本。
株洲市國資委統一將“合同編號”“支付對象”“銀行流水號”設為三大關鍵標識字段,強制所有系統按標準輸出數據。
第二步是“AI織網”。株洲國資國企資金監管系統構建了18項風險指標模型,例如“超合同支付”自動關聯施工進度,“對私轉賬”比對員工親屬關聯企業。2025年4月,該系統試運行首周便發出預警:某三級公司向一家注冊資本僅50萬元的勞務公司單筆支付2000萬元。經核查,該勞務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子公司高管親屬。
至2025年6月20日系統上線時,該系統已歸集2023年以來的31萬筆支付記錄,涉及資金超8000億元。監管響應速度從“按月”壓縮至“分鐘級”。
上述當地市屬國企副總經理表示,自己所在企業,過去迎檢需準備超千頁紙質資料,如今系統10分鐘生成合規報告。
集團數據貫通
2025年3月,上述能源企業財務負責人徐佳明,在月度經營分析會上遭遇了尷尬一幕:集團總部下發的“全級次穿透監管”指令要求實時上報資金流向,但他的團隊卻仍在手工匯總7套系統的數據。
他說:“采購系統顯示已付款,財務系統卻查無此賬,最后發現是子公司用獨立ERP做的賬,數據根本沒同步。”
該能源企業是西南區域的重要煤炭采購平臺,年交易規模超200億元。然而,其信息化建設卻如同“打補丁”,2010年上線SAP財務系統,2015年引入用友供應鏈模塊,2018年并購的物流公司仍在使用金蝶K3,而基層煤礦甚至依賴Excel臺賬。
上述周姓物流負責人說:“最離譜的是,同一個‘煤炭庫存’,在財務系統里叫‘存貨’,在供應鏈系統里是‘在途物資’,到了物流系統又變成‘待驗收煤’。”
徐佳明翻出2024年審計報告:因數據口徑混亂,公司當年合并報表延遲45天,導致集團誤判西南區域煤炭儲備,超采30萬噸,造成6000萬元資金占用成本。
他認為,更大的風險藏在業務鏈深處。
2024年9月,一家與其長期合作的貿易商突然被列入失信名單,但企業采購系統仍自動向其支付了1.2億元預付款。
轉機來自2025年集團的“數據貫通”命令。
第一仗是強制統一數據標準,集團要求所有子企業系統按標準輸出。第二仗是搭建“數據中臺”。系統引入校驗模型,例如“付款金額大于合同價”自動觸發預警,“供應商與員工姓名相似度大于70%”提示關聯交易風險。試運行首月,系統查驗出某煤礦向高管親屬控制的企業集中采購的線索,涉及金額2.8億元。
截至2025年6月底,該能源企業已完成5.6萬筆歷史數據清洗,核心業務數據貫通率達92%。
數據權與經營權的“楚河漢界”
并非所有企業都能接受這種“透明”。
上述能源企業總經理表示:“現在買根鋼管都要審批,項目推進出現了新障礙。”
他負責的貴州電廠項目因“超合同支付”被系統攔截3次,工期延誤兩個月。最終集團與之協商:對境外項目、金融衍生品等高風險領域實施實時監控,而對基建、采購等常規業務改為“T+1”抽查。
上述總經理認為,更深的矛盾在于考核機制。
2025年半年報顯示,上述能源企業因數據治理投入增加管理費用3200萬元,但同期風險損失下降1.7億元。
徐佳明說:“總部集團仍按傳統財務指標考核我們,數據治理的‘隱性收益’根本體現不到績效上。”
經濟觀察報獲悉,這一問題在其所在的央企集團2025年內部調研中,曾被多次提及,但目前尚未有調整方案。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其他國企和央企中。
全級式穿透管理推廣初期,一家基建國企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開放采購數據,地方國資委人士親赴談判:“我們可以設置分級權限,涉及戰略投資的數據僅向省國資委開放,但資金安全紅線必須全域監管。”
最終達成一致:該系統開放9類資金數據,但技術研發賬戶暫不納入。
還有“權責重構”的問題。
一家建筑企業原財務總監說:“子公司付筆工程款都要被市里預警,我們還怎么靈活經營?”
上述國務院國資委人士認為,株洲的解決方案可以借鑒,比如推進分類監管,對高風險企業實施高頻核查(如每月審計資金流水),低風險企業則減少干預。
盡管穿透式監管能覆蓋的資金場景越來越多,但上述地方國資委人士表示:“真正的穿透才剛開始。”
2025年7月,一家國企境外子公司通過離岸架構投資光伏項目,因當地數據隱私法限制,資金最終流向無法追蹤。
該國企綜合辦公室主任說:“這類項目占我們監管盲區的60%以上,只能依賴事后審計。”
在寧夏國資委的穿透式監管平臺上,全區278戶國企的1711個銀行賬戶雖被實時監控,但重大投資決策仍依賴人工上報。“比如企業收購一家科技公司,系統能看到資金流出,卻無法判斷技術估值是否合理。”
寧夏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將打通投資評審系統,對“三重一大”事項實施全鏈條存證。
穿透的邊界
?
2025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楊繼東在《國有企業數字化監管的有效性研究》報告發布會上說:“穿透式監管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對過去十年國企改革痛點的集中回應。”
國務院國資委此次發力,基于多重考量。比如風險傳導失控,相關央企境外資產因數據斷鏈形成的風險敞口;比如監管滯后失效,在傳統“報表監管”模式下,重大風險平均發現周期達3個月,有能源集團甚至因數據孤島未能及時發現子公司5.6億元的關聯交易。此外,改革倒逼升級:隨著國企混改深化,股權結構復雜化使得“影子股東”“隱形控制”問題凸顯,穿透式監管成為厘清權責的關鍵工具。
上述國務院國資委人士認為,國務院國資委“穿透式監管”新規全面落地,央企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數據革命。這場變革背后,既有監管層對系統性風險的深度憂慮,也有企業對經營自主權的現實焦慮。
該人士表示,即便方案明確,但還有商榷之處。
2025年7月,一家建筑央企國際業務部總經理在座談會上發問:“當我們在境外的合資公司因當地數據法規無法回傳信息時,算不算監管失敗?”
對此,一名國資人士現場回應:“穿透式監管不是萬能鑰匙,境外數據需通過區塊鏈存證等變通方式解決,但核心紅線不能突破。”
還有創新成本的痛點。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李青原在2025年4月的研討會上說:“若對商業一類(競爭類)國企管得過細,可能扼殺其市場響應速度,與‘原創技術策源地’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上述國務院國資委官員表示,這場監管革命遠未結束,在“放活”與“管好”間,想走好這根鋼絲,要掌握好平衡,明確穿透式監管框架的核心爭議,究竟在哪些方面。
盡管穿透式監管已覆蓋大部分境內央企和國企,但一家央企總會計師認為,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他說:“我們現在能看到資金流水,但還看不懂業務實質。比如某筆海外并購溢價30%,系統只會報警,卻無法判斷是戰略需求還是利益輸送。”
該總會計師認為,上述局限也暴露在審計過程中。
2025年6月,該總會計師發現,下屬子公司通過“循環貿易”虛增營收15億元,交易結構藏在合同補充協議里,AI(人工智能)模型只能抓取主合同數據。
截至2025年8月,上述總會計師所在央企,已經為穿透式監管投入超10億元,攔截風險交易逾300億元。
上述國務院國資委官員表示,目前,穿透式監管的核心爭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比如監管訴求和企業痛點之間的博弈、風險可控性和數據治理成本之間的矛盾、權責清晰化和經營靈活性之間的平衡、全局可視化和境外合規沖突之間的把控等。
上述國務院國資委人士補充說:“穿透式監管的終極目標,是讓央企既能‘看得見風險’,又能‘跑得出速度’。”
而找到那條精準的平衡線,才是真正的考驗。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佳明為化名)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