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關注
2025-08-06 12:27

![]()

得知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以安樂死的方式離世的消息,是在去年3月底一個清冷的早晨。那本早已翻舊的《思考,快與慢》依舊擱在我的書桌,書頁折了多處,有些頁碼邊緣微微卷起,使得整本書膨脹得有點像發酵過的面包。是的,對我來說,卡尼曼先生,這位遠在彼岸的智者,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位“知識面包師”。我關于行為經濟學那點粗淺的認知骨架,很大程度上是啃了他的幾本著作,尤其是這本“面包書”,才勉強支撐起來的。它填充了我對“人如何決策”這一古老命題理解上的巨大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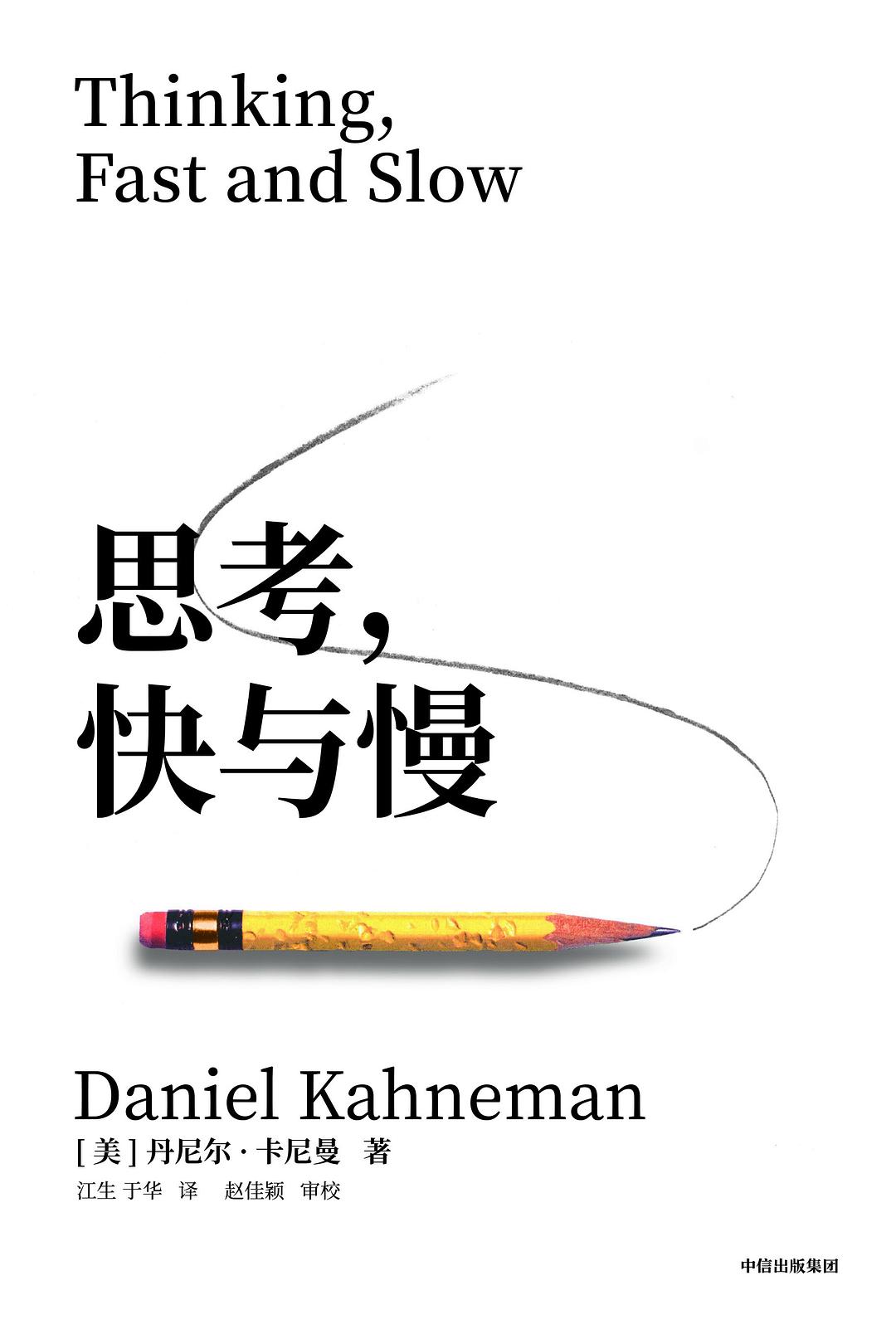
《思考,快與慢》
[美] 丹尼爾·卡尼曼| 著
江生 于華|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4月
更重要的是,正是他交給我的底層邏輯,觸發了一系列難以抑制的新思考,催生出一種近乎迫切的表達欲。10多年前,在經歷了一段職業轉換和思想的倦怠期后,我本已主動停掉了在《北京青年報》上持續多年的專欄寫作。然而,卡尼曼的一系列洞見,像一把鑰匙,重新擰開了我觀察世界的閥門。街角小販的討價還價,同事會議上的爭執不下,新聞里政策出臺后的眾生百態,甚至我自己面對選擇時的躊躇……都似乎有了一個更貼近人性本真的解讀視角。
這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夾雜著分享的沖動,竟讓我腆著臉皮又找到了《北京青年報》評論部供職的雜文家潘多拉兄,請求恢復專欄寫作。所幸,老友寬容。于是,在停筆近兩年后,我的文字又斷續地見報了,而那一時期的專欄主題,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在嘗試用卡尼曼提供的“行為經濟學”的框架,解析我所看到的人間萬象。現在,這位為我源源不斷供給思想營養的面包大師,已然在89歲高齡選擇了離席。我必須要為他寫點什么,權當是對這位智者的一份微薄祭奠。
一
卡尼曼之于行為經濟學,其功勛堪稱奠定了整座大廈的基石。這位心理學家出身的經濟學家,與他一輩子的摯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一起,以精湛的專業領域知識以及無可辯駁的一個個社會實驗,冷靜而精準地揭露了新古典經濟學用看似雅致的數學模型構筑的完美“理性人”背后的虛幻。他們的研究揭示:人,絕非冰冷的、精于計算的邏輯機器。在面對得失權衡、風險抉擇時,我們的心智更像一個搖擺不定的鐘擺,在“規避損失”與“追逐收益”“冒險一搏”與“保守求穩”之間反復震蕩,其軌跡充滿了非邏輯的波動。
這就是卡尼曼的偉大之處:把我們從黑板經濟學構造的“理性”幻境,拉回到一個幽深晦暗、卻無比真實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盤踞著無數看不見的“認知幽魂”——“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讓我們不自覺地被初始信息所綁架,哪怕它荒誕不經;“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Heuristic)讓我們依據記憶中最容易提取的、而非最準確的信息來判斷概率,恐懼常因此被放大;“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則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失去100元帶來的痛苦,其強度遠超獲得150元帶來的喜悅,這使得我們常常在變革面前裹足不前,寧可忍受已知的困苦,也不愿踏入未知的改善。
還有“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讓我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估值過高;“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讓我們在諸多領域(尤其是預測未來時)高估自己的準確度;“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僅僅因為信息呈現方式的不同(如“存活率90%”vs “死亡率10%”),就能輕易改變我們的選擇……這些無形的幽靈,在我們意識的暗處低語、牽引,無聲無息地將我們引向非理性的歧途,而我們往往對此渾然不覺。
這豈非正應和了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中的喟嘆:“世界不過是一座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只是些演員”?我們這些匆忙登臺的演員,在名為“生活”的宏大劇目中,何嘗不都在被這些根植于大腦深處的認知偏差所導演,上演著一幕幕不自知的悲喜劇?
卡尼曼,這位冷靜近乎冷酷的觀察者與實驗者,用嚴謹的心理學實證方法,為我們徐徐揭開了這舞臺后臺的幕布,讓我們得以一窺那操縱著萬千絲線的復雜機關。他讓我們明白,許多看似愚蠢或不可理喻的行為,背后往往有其深刻且普遍的心理機制,而非簡單的道德瑕疵或智力不足。
二
卡尼曼這種穿透表象、直抵人性幽微之處的洞察力,絕非憑空降臨的學術天賦。其淵藪,深深植根于他生命早期所遭遇的驚濤駭浪與殘酷淬煉。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在其精彩著作《思維的發現:關于決策與判斷的科學》(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中,為我們披露了卡尼曼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與學術心路。
少年卡尼曼,身為猶太人,其童年便在納粹陰云的籠罩下度過。最令人心悸的記憶定格在1941年納粹占領下的巴黎。年僅7歲的他,在一個夜晚被父親從睡夢中急促搖醒。沒有多余的解釋,只有一句冰冷、沉重、足以壓垮任何童稚心靈的生存箴言被反復灌輸:要想活下來,就不能相信任何人——鄰居、朋友,甚至街上的陌生人,都可能成為告密者。
他被父親迅速藏匿于公寓的地板之下一個狹窄、黑暗、充滿塵埃的夾層空間里。在那里,他蜷縮著幼小的身體,心臟狂跳,幾乎不敢呼吸,只能豎起耳朵,屏息凝神地捕捉著地板之上那個“正常”世界里傳來的每一絲聲響:靴子踏過樓板的沉重腳步、粗暴的敲門聲、斷斷續續的德語呵斥、鄰居壓抑的哭泣……這一切,塑造了他對人性之不可測、世界之兇險的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認知。這種在極端恐懼下對“信任”的徹底剝奪,以及對環境極度警覺的生存狀態,無疑為他日后研究人類在壓力、不確定性下的判斷與決策偏差,埋下了最原始也最真切的伏筆。
僥幸逃離法國后,少年卡尼曼隨家人輾轉來到當時英國委任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然而,安寧并未如期而至。他旋即又親歷了以色列建國之初的烽火連天。青年時期,他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服役,參與過培訓飛行員的心理學評估工作。戰爭的硝煙、生命的脆弱、集體狂熱與個體恐懼的交織、在生死攸關的壓力下人們決策的種種變形……都成為他觀察人類非理性行為的天然實驗室。
這種雙重淬煉——納粹陰影下的個體生存掙扎與建國初期集體命運的抗爭——使他對人性之幽微復雜與命運之無常詭譎,擁有了刻骨銘心、遠超書本的切膚體察。他不僅洞悉了人類個體在極端壓力下抉擇的脆弱本相,更在自身的情感與立場上經歷了深刻的撕裂。
這種撕裂在他對待故國以色列的態度上體現得尤為微妙而執拗。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之日,當時正在美國訪學的卡尼曼,盡管對這場戰爭的爆發有諸多疑慮,但強烈的同胞情感和對以色列存亡的憂懼,促使他幾乎毫不猶豫地輾轉萬里,第一時間返回戰火紛飛的祖國,希望能為同胞盡一份心力。
然而,戰爭結束后,以色列政府拒絕歸還戰爭中非法占領的阿拉伯領土,以及戰爭中針對阿拉伯平民的某些殘酷行徑,又讓他感到深深的失望與道德上的不適。這種內心的沖突最終促使他做出了一個看似矛盾的決定:他借由第二次婚姻的機會,選擇了徹底離開以色列,定居美國。
這并非尋常意義上的怯懦或逃避,而是一個深切理解人性之復雜(包括民族情感與暴力沖動)、對“正義”與“生存”有著痛苦權衡的靈魂,在巨大的歷史洪流裹挾下做出的艱難抉擇。這種選擇本身,正是其理論中“系統一”(System 1)——基于情感、直覺、身份認同的快速反應——與“系統二”(System 2)——需要審慎思考、道德判斷的緩慢認知——之間激烈交鋒的活生生寫照。他理解個體在戰爭機器前的渺小無助與情感驅動,同時也難以割舍對同胞命運的關切,更無法違背內心對某種普遍道義原則的堅持。這種內在張力伴隨了他的一生。
更有意味也更具悲劇色彩的是,卡尼曼晚年的思索,如同潮水退去后裸露出的黑色礁石,顯露出另一層深邃的憂思與無力感。他開創的行為經濟學革命,初衷是幫助人們認識自身的認知局限,從而做出更好的決策,獲得更自由、更明智的人生。
然而,他無奈地目睹著自己揭示的人性弱點,被資本與權力的巨輪無情地裹挾、利用。那些耗費他畢生心血研究的認知偏差——錨定效應、損失厭惡、社會認同(Social Proof)、稀缺性(Scarcity)……非但沒有成為人們武裝自己、抵御操控的盾牌,反而成了商業巨頭精心設計消費陷阱的利器,成了政治操弄者煽動情緒、引導輿論的杠桿,更成了互聯網巨頭用算法編織信息繭房、精準推送、誘導沉迷、榨取注意力和數據的核心密碼。
因此,卡尼曼曾不無沉痛地慨嘆:“我們(行為經濟學家)揭示了人性弱點,卻未能賦予人們足夠的抵御之力。” 這句沉甸甸的話語,猶如《浮士德》中梅菲斯特那充滿嘲諷的低語——知識縱然偉大,光芒萬丈,卻未必總能導向善的路徑,甚至可能成為更精巧作惡的工具。
卡尼曼思想中那束曾經照亮人類認知迷霧、旨在帶來解放的理性之光,在現實世界的復雜博弈中,被無情地扭曲、折射、利用,最終竟異化成了新的、更為隱蔽和高效的操控工具,被資本與權力的巨手所肆意濫用。這無疑是一個充滿辛辣諷刺的悖論,他窮盡智慧試圖理解人性、改善決策,卻最終收獲的是未曾料想到的苦澀果實。
三
最終,卡尼曼以89歲高齡,選擇了自我意志的歸途。這個結局本身,宛如其輝煌學術生涯的一個極致隱喻,一個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注腳。他畢生致力于研究人類決策中的非理性暗礁,揭示那些將我們引向歧途的認知陷阱,孜孜不倦地提醒世人警惕“快思”(系統1)的直覺陷阱,呼喚“慢想”(系統2)的審慎光芒。然而,這位洞悉了人性迷宮所有曲折暗道的大師,最終卻以一種被世俗視為最需要理性決斷、最需要克服本能恐懼(對死亡的恐懼)的方式——自主結束生命——離開了這個充滿了“噪聲”(Noise,他晚年另一重要研究主題,指判斷中不必要且有害的變異)、混亂與非理性的世界。
這決絕的轉身,留給世人無盡的叩問:他是否在生命的終點,以終極的實踐,驗證了人類在絕對孤獨與終極命題面前理性框架本身的脆弱性?抑或是,他通過這最后的抉擇,終于徹底擺脫了“快思”的直覺沖動(對生的本能眷戀)與“慢想”的審慎權衡(對責任、后果的無窮思慮)那永無止境的撕扯與煎熬?他是否由此逃離了那個他親手描繪得無比清晰的“認知牢籠”,抵達了一種終極的、永恒的“認知放松”(Cognitive Ease)?在那里,不再有偏差的困擾,不再有決策的負擔,不再有系統1與系統2的永恒角力?對這一切,我們當然無從確知。
斯人已逝。書桌上,卡尼曼的代表作《思考,快與慢》依舊靜靜地攤開在案頭。春早的陽光斜射進來,落在略顯陳舊的書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筆記和折痕在光線下顯得格外清晰。昔日在我眼里的知識面包,此刻也仿佛一座無聲的紀念碑,紀念著這位曾以無與倫比的智慧與勇氣,為我們解析人類心智迷宮、最終卻選擇以一種最令人深思的方式悄然走出這座迷宮的思想巨匠。在認知偏差的盡頭,卡尼曼不僅留下了他的行為經濟學思想遺產,更留下了諸多關于理解、關于局限、關于自由、也關于生命尊嚴的永恒話題,考驗著仍在迷宮中摸索前行的我們。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8547號